三峡移民纪录片有哪些
五月初的涪陵,时阴时雨时艳阳,天气就象一个正值青春期的少年,时不时的要耍耍小性子。
凌晨4点多,睦和村还在大江的臂弯中沉睡,我和导演一行人等便匆匆告别周公,披着满天星斗上路了。
睦和村的日出是导演张道伟想要捕捉的镜头。伟哥是个有思想有情怀的导演,一米八三的身材高魁伟岸,我曾戏言他的体积有175的库容,这也是三峡大坝蓄水时的最高水位线。

与伟哥谈创作,他常常提到的一个词汇就是“乡愁”。我跟他一样,也喜欢这个调调,喜欢把这种情愫移植在纪录片里!这种情愫虽然会带有“小我”和“呢喃”的色彩,但也会得到很多观众的共鸣,尤其是那些游子们,当然也包括那些为了三峡工程默默奉献,而背井离乡的三峡移民。

车至山脊天光渐白,我们扛起设备疾奔山顶。树枝间草叶上的露珠像细碎的琉璃纷纷滚落,顷刻间便打湿了鞋面至膝头。气喘吁吁的我们架好机器准备拍摄,当大家抬头远眺时,那喷薄欲出的太阳呢!

烟笼江水,雾锁远山,迷迷茫茫如临仙源。浓重的白雾像帷帐一样,把早起的太阳裹挟得没了踪影,连前方不足百米远的大树都虚幻模糊了。伟哥垂头,小雷低首,我们怅然了……

天公不眷早起人,伟哥不甘要苦等。我这牛脾气也上来了,就不信你不露头,一个字“等”!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太阳就是那么任性的躲在云层后,隐在迷雾中,好像在故意戏弄着我们这几只早起的鸟!时近七点,雾气不但没消散,反而越来越浓重了。不多时,淅淅沥沥的雨滴从空中坠落下来,我们仅有的一点希望也被这雨水彻底浇灭了!怏怏的收拾好器材走下山坡,心情低落到了极点。
回到驻地,追求完美的伟哥郁闷地坐在棚檐下,我按下相机快门,给他留下了这个情绪的瞬间。

睦和村的雨就这样由着性子的从早上飘到了午后,临近下午4时许戏虐了近一天的雨,终见没人理会它,便悻悻的收了场子!
雨刚刚一停,那些蛰伏起来的鸟雀们便赶集一样冲进了天空,开始了一场饕餮大宴!追花人饲养的蜜蜂也嗡嗡出巢了!
伟哥的思路很是灵活,虽然早上没能拍到日出,他很快就把工作调整到次日拍摄长江开鱼的准备活动中。那是一个相对场面较大的两场戏:江上渔者和江岸渔火!

漫步在雨后的乡村,湿漉的不仅仅是村庄还有人的心情。一只黑鸡呆立在桑树下,偶有声响,也只是象征性的翻一下眼皮,然后就自顾自的发呆去了。一条黄狗用爪子挠了挠耳朵,抖了抖身上水气,无精打采的走进了家门。透过一户敞开的门庭,简单而零散的家居孤独的摆在那里。

没有人的院落,少了生气的村庄,连屋檐下滴落的雨水都带着种淡淡的忧愁。村里面见到最多的就是老人和孩子,年轻人都出外打工挣钱去了!这里微缩了当代中国农村的现状,空巢老人,留守儿童已经成了当今社会无言的痛。

漫步途中,看到一个小女孩儿在墙边独自玩耍,脏兮兮的小手里拿着一只饮料瓶在往里面装土玩儿!见我过来,她忙起身看着我,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透视着朴素的纯净!小女孩儿没有说话,只是朝我甜甜的笑着,小脸上洋溢着山村的淳朴!这也该是个留守儿童吧,她的爸爸妈妈又在哪里呢……做为一个父亲我的心揪得很紧很紧!

顺着长满杂草的小路,我缓缓的走向江边。途径一户人家,一位老者正坐在门前凝望。见有人来老人也忙起身打招呼。

老人说着一口川渝方言,有些话我虽然听不太懂,但从他的表情中我读出了喜悦和热情。他从院子里的枇杷树上摘了两只枇杷塞给我。说到:“你们是远道来的客人,尝尝吧”!

我们到睦和村拍摄也有两天了,老人大概也知道了我们。老人说他今年74岁了,身体很好,政府给上了医疗保险,每月还能领1000元的补助,他生活得很幸福。还说他有个儿子跟我差不多一样大,在广西打工。老人也许是久没跟外人说过这么多话了,见到了我就打开了话匣子……我半懂半猜的跟老人交谈着,透过他那张饱经风霜的脸,带着幸福和满足的同时,眼神间也不经意流露出一种淡淡的孤独!

告别老人,手里托着那两只黄橙橙的枇杷,喉咙紧紧的,心头空空的!空荡荡的院落,独自玩耍的小女孩儿,孤独的老者,一股《乡愁》慢慢弥上了心头:多少年的追寻 ,多少次的叩问。乡愁是一碗水,乡愁是一杯酒。乡愁是一朵云,乡愁是一生情。年深外境犹吾境,日久他乡即故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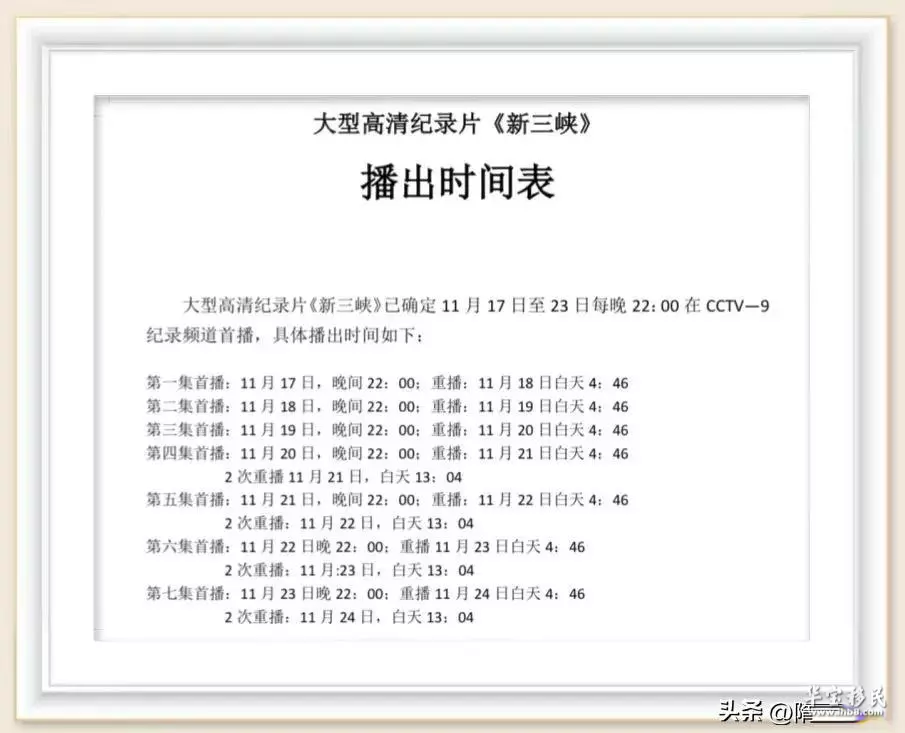
相关文章
-

三峡移民到广东有多少人(摄影师记录百万三峡移民)
重庆三峡移民纪念馆外观本文图片均由重庆三峡移民纪念馆提供东汉灰陶庖厨俑“三峡外迁移民第一人”徐继波捐赠的外迁船票以身殉职的巫山移民干部冯春阳生前用品正是三峡库区最美的时节,高峡出平湖,碧绿长江滚滚而来。江水之畔,矗立着一座巨石般的建筑,这就是重庆三峡移民纪念馆(重庆市万州区博物馆)。20多年前,举世瞩目的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动工。
2023-12-21 阅读 (26) -

三峡移民是怎么安置的(三峡工程的移民都去了哪里)
【关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使,及时获取国际教育,科技,文化,经济及世界语(esperanto)最新资讯】三峡工程是世界上最大的水电工程,其建设时间之长、建设难度之大、涉及难题之多,是全世界范围内都不曾遇到过的。这其中,最大的困境,恐怕还在于水库修建区域的大量居民应该如何疏散。上百万人,背井离乡,如果得不到很好的安置会成为巨大的不稳定因素,而如果妥善安置则不仅能完成项目,还能作为中国管理水平的样本以鉴后世。
2023-10-23 阅读 (26) -

三峡移民上海多少人(百万三峡移民)
重庆日报全媒体龙丹梅110多万移民告别故土,2座城市、7座县城、94座集镇迁建,1400家工矿企业搬迁……这不是一组简单枯燥的数字,这是重庆为三峡工程按期蓄水、通航、发电作出的巨大牺牲和贡献!三峡工程成败的关键在移民,而移民的重点在重庆,重庆承担着85%以上的三峡移民任务。自三峡工程移民搬迁安置工作启动到全面完成移民搬迁安置任务,重庆累计搬迁安置移民110万余人。
2023-11-08 阅读 (20) -

三峡移民纪录片有哪些
五月初的涪陵,时阴时雨时艳阳,天气就象一个正值青春期的少年,时不时的要耍耍小性子。凌晨4点多,睦和村还在大江的臂弯中沉睡,我和导演一行人等便匆匆告别周公,披着满天星斗上路了。睦和村的日出是导演张道伟想要捕捉的镜头。伟哥是个有思想有情怀的导演,一米八三的身材高魁伟岸,我曾戏言他的体积有175的库容,这也是三峡大坝蓄水时的最高水位线。
2023-12-03 阅读 (20) -

三峡移民是哪些地方迁移出去的(三峡工程的移民都去了哪里)
【关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使,及时获取国际教育,科技,文化,经济及世界语(esperanto)最新资讯】三峡工程是世界上最大的水电工程,其建设时间之长、建设难度之大、涉及难题之多,是全世界范围内都不曾遇到过的。这其中,最大的困境,恐怕还在于水库修建区域的大量居民应该如何疏散。上百万人,背井离乡,如果得不到很好的安置会成为巨大的不稳定因素,而如果妥善安置则不仅能完成项目,还能作为中国管理水平的样本以鉴后世。
2023-10-03 阅读 (31) -

三峡移民移到哪了(他们移向了哪里,如何重新扎根)
【关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使,及时获取国际教育,科技,文化,经济及世界语(esperanto)最新资讯】三峡工程是世界上最大的水电工程,其建设时间之长、建设难度之大、涉及难题之多,是全世界范围内都不曾遇到过的。这其中,最大的困境,恐怕还在于水库修建区域的大量居民应该如何疏散。上百万人,背井离乡,如果得不到很好的安置会成为巨大的不稳定因素,而如果妥善安置则不仅能完成项目,还能作为中国管理水平的样本以鉴后世。
2023-10-11 阅读 (62) -

三峡移民搬到上海什么地方(20年前三峡移民到上海)
引言采访三峡外迁上海的移民中,刘叔是我遇到的一位态度非常“强硬”的人,采访过程中,刘叔甚至直接喊出,我就是上海人,我死都要死在上海。而关于他的故事,也让我非常感动,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他的故事吧。今天我来到上海嘉定区的娄塘镇,据说这里在2004年的时候,接收了很多来自三峡库区的移民。2004年 9月1日,重庆云阳县的刘建军(故事里我们称刘叔)背着龙凤胎儿女抵达上海。
2023-11-08 阅读 (30) -

加拿大移民生活纪录片(移民加拿大18年)
这是我们讲述的第1208位真人故事我叫李忠学@才思敏捷的田舍翁,1969年出生于云南西双版纳,现定居温哥华。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深山发电厂当了一名监控技术员。后来为了更好地发展,我带着全家移民到了加拿大,干过汽配厂电工、油砂电工、污水处理厂电工,还卖过水机,送过外卖......这种生活老婆根本无法适应,于是带着孩子回了国,最终因长期两国分居,导致感情破裂而离婚。
2023-10-12 阅读 (36) -

三峡移民后来怎么样了(摄影师记录三峡移民27年)
2019年冬天,一张一个男人背着一树桃花的照片,忽然出现在互联网上,击中了许多中国人的心。照片的主人公,是来自湖北秭归县郭家坝镇的山民,刘敏华。十年前的春天,作为三峡库区移民的刘敏华,「在与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永别时,小心翼翼地带上了家门口的一棵桃树」。 ①屋檐下静默的男人,和他狭长背篼里那株盛放的桃花,激起观看者胸中无限心事。
2023-10-30 阅读 (26) -

三峡移民安徽哪个村最好找工作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融媒体系列报道《我和我的党支部》 今天,为您带来由湖南电台携手重庆市万州区广播电视台等全国100家电台采制的《五溪村党支部:带领三峡移民“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人间最美四月天。在重庆市万州区新田镇五溪村,满目果树繁茂,阵阵花果飘香,一江碧水,两岸青山,一副生机盎然的山水画卷展现在前来采摘的游客面前。
2023-09-28 阅读 (42)
热门资讯
-
 2023-10-13 阅读 (155)
2023-10-13 阅读 (155) -
 2023-10-17 阅读 (147)
2023-10-17 阅读 (147) -
 2023-10-18 阅读 (90)
2023-10-18 阅读 (90) -
 2023-10-23 阅读 (88)
2023-10-23 阅读 (88) -
 2023-12-04 阅读 (80)
2023-12-04 阅读 (80)
最新资讯
-
 2023-12-27 阅读 (15)
2023-12-27 阅读 (15)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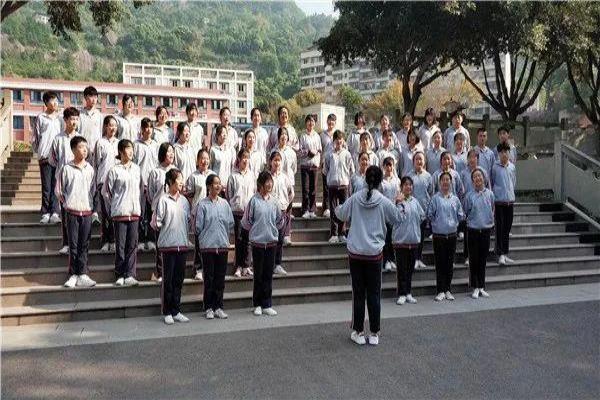 2023-12-26 阅读 (21)
2023-12-26 阅读 (21) -
 2023-12-22 阅读 (21)
2023-12-22 阅读 (21) -
 2023-12-21 阅读 (25)
2023-12-21 阅读 (25) -
 2023-12-21 阅读 (26)
2023-12-21 阅读 (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