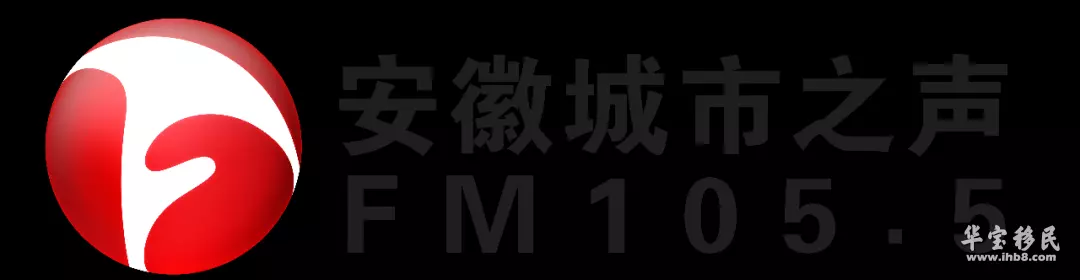三峡移民安徽哪个村最好找工作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融媒体系列报道
《我和我的党支部》
今天,为您带来由湖南电台携手重庆市万州区广播电视台等全国100家电台采制的《五溪村党支部:带领三峡移民“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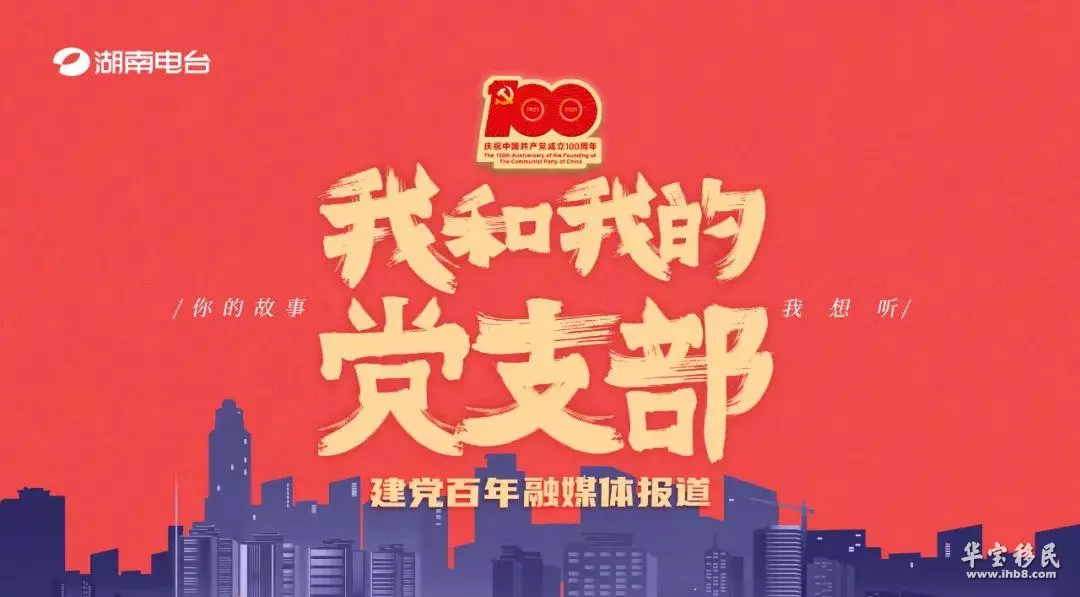
人间最美四月天。在重庆市万州区新田镇五溪村,满目果树繁茂,阵阵花果飘香,一江碧水,两岸青山,一副生机盎然的山水画卷展现在前来采摘的游客面前。
△柠檬花开
“今天休息,专门过来摘沃柑的,而且你看那边的柠檬树开花了,等结了果我还要买些回去做柠檬茶,很好喝。”游客告诉记者,这里风景好、空气好,土地也肥沃,种出来的水果品质非常好。
△挂满花苞的柠檬树
然而,谁能想到游客们赞不绝口的这片花果园,多年前曾是一片乱石岗。
△五溪村以前乱石林立
万州,是三峡库区移民人数最多、移民任务最重的城市。当三峡工程蓄水到135米时,五溪村所涉及的8个组、150户村民们成为了三峡移民工程最早的一批移民。在村党支部的带领下,乡亲们从水土丰沃的长江边搬到乱石林立的荒山坡“黑儿梁”,党员干部带头开辟荒山建果园,发展林果经济,使昔日的荒山坡变成了今日的金山银山,五溪村也从十几年前的“移民村”发展成如今远近闻名的“幸福村”。
农村富不富,关键看支部。五溪村党支部一班人都意识到,不仅要带领乡亲们搬得出,还要稳得住、能致富。村党支部不约而同想到了发展林果经济,既可以守住这一江碧水、两岸青山,又能为村民带来持续的收益。
△召开院坝会,解决村民种植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可是,种惯了庄稼的村民们担心种果树风险大,收益慢,无论他们怎么劝说,乡亲们依然踌躇不决、保持观望。时任五溪村村长、现五溪村党支部书记冉振爱说,“支部强不强,要靠‘领头羊’”,于是他决定自己来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不仅如此,在冉振爱的带领下,五溪村党支部多次邀请农业果树专家为大家进行技术培训,手把手指导,还对村里的贫困户免费送果苗、送技术的方式给予帮扶,很快,原本不被看好的荒山荒坡变得瓜果飘香。
但由于村民们自发种植的果树品种繁杂,无法形成规模优势和市场优势。在镇党委、政府的支持下,经专家科学论证,五溪村党支部和村里干部与群众一起协商后达成共识:引进发展优质柠檬。
△柠檬专业合作社技术人员现场演示套袋技术
随着柠檬面积不断扩大,2014年,五溪村党支部发起成立了专业合作社,指导村民规模化种植。五溪村幸柳柠檬专业合作社技术员冉振洪自豪地说,五溪村几乎家家户户种上了柠檬,肥料统一购买,外出务工农户的柠檬也由合作社统一管理,全村实施了标准化生产,提高了柠檬品质,注册了商标,增强了市场竞争力。
△冉振爱为种植户介绍果树养护知识
现在,五溪村长江沿岸、公路两边、房前屋后,6000亩优质柠檬树连片成林,宛若一条铺在长江边上的绿色屏障,不仅绿化了江岸,美化了家园,还固土防沙、保持水土,更是为村民带来了可观收入,实现了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
生态好了、环境美了、村民富了。冉振爱告诉记者,五溪村6000亩优质柠檬盛产时产量达到500万公斤,年销售收入超过2000万元,带动了包括8户建卡贫困户在内的800多户村民人均增收8000多元,柠檬树已变成了村民的“摇钱树”。
△五溪村柠檬丰收了
在村里的柠檬产业初具规模后,五溪村党支部并没有满足现状,又结合退耕还林,在海拔400米以上3000亩坡地上种上了抗旱能力强、管护容易的麻竹。如今,连片的竹海绿浪滚滚,既稳固了山石,保持了水土,还带来了经济效益。
△连片成林的果树宛如一条绿色屏障
“在村支部带领下种植柠檬,我种了3亩多,每年能卖2万左右。后来干部们又提倡在坡上空地上种麻竹,那个容易管理,光卖笋子一年可以卖几千块钱。跟着党组织选对了种植的路,确实还是可以,哈哈。”望着今年即将丰收的果园,村民何先华高兴地说。
△重庆市万州区新田镇五溪村党支部合影
昔日乱石岗,今日花果园。在五溪村党支部的带领下,如今的五溪村,产业兴、生态美、百姓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是这里最真实的写照。
相关文章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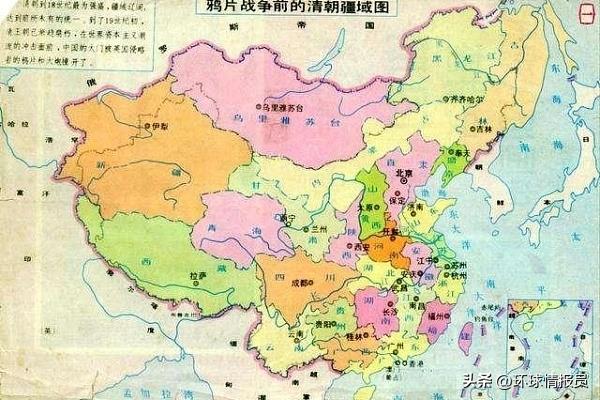
三峡移民为什么去外省(以宜昌为省会的三峡省为何“胎死腹中”)
增减省级行政区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中国现有的34个省级行政区之中,除了1997年设立的直辖市重庆、1988年设立的海南省外,其他省区的总体架构和数量,在清朝前期便已基本固定了下来。▲现在中国的省份名字和区划,大体在清朝就已经固定了下来民国中后期及新中国初期,是又一个省区频繁增设或撤销的历史时期,涉及西康、察哈尔、绥远、平原、松江、辽东、辽西、宁夏等9个新省区。
2023-10-11 阅读 (41) -

三峡移民是哪些地方迁移出去的(三峡工程的移民都去了哪里)
【关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使,及时获取国际教育,科技,文化,经济及世界语(esperanto)最新资讯】三峡工程是世界上最大的水电工程,其建设时间之长、建设难度之大、涉及难题之多,是全世界范围内都不曾遇到过的。这其中,最大的困境,恐怕还在于水库修建区域的大量居民应该如何疏散。上百万人,背井离乡,如果得不到很好的安置会成为巨大的不稳定因素,而如果妥善安置则不仅能完成项目,还能作为中国管理水平的样本以鉴后世。
2023-10-03 阅读 (33) -

三峡移民后来怎么样了(摄影师记录三峡移民27年)
2019年冬天,一张一个男人背着一树桃花的照片,忽然出现在互联网上,击中了许多中国人的心。照片的主人公,是来自湖北秭归县郭家坝镇的山民,刘敏华。十年前的春天,作为三峡库区移民的刘敏华,「在与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永别时,小心翼翼地带上了家门口的一棵桃树」。 ①屋檐下静默的男人,和他狭长背篼里那株盛放的桃花,激起观看者胸中无限心事。
2023-10-30 阅读 (26) -

三峡移民为什么要外迁(库区外迁移民)
三峡库区农村外迁移民车队2000年8月13日,是个令人难忘的日子。这一天,重庆三峡库区首批7000多外迁移民,在各级政府精心组织下告别祖祖辈辈休养生息的故土,走向新生活。这一天,重庆三峡库区数县的农村兄弟,扶老携幼,在送别的亲友簇拥下,一步三回头,乘上汽车,坐着轮船,奔赴陌生的天地……别了,我的乡亲
2023-11-27 阅读 (23) -

万州三峡移民事件(摄影师记录三峡移民27年)
12019年,一个老汉背着一树桃花的照片,击中了很多中国人的心。背桃树的移民十年前他作为三峡库区的移民,穿着解放鞋、背着这树桃花在屋檐下沉默了好久,最终含着眼泪踏上了一条陌路。他叫刘敏华,是北秭归县郭家坝镇的山民。而这张照片的背后,还有与他同样经历搬迁的百万余人。每一帧都在诉说着一段历史的变迁与难以言说的心酸.......
2023-12-17 阅读 (25) -

三峡移民去哪了(20年前从三峡库区搬迁山东的移民)
2004年8月5日,一列满载三峡移民的列车先后于早晨和中午停靠到了邹城、兖州和济南火车站,新增三峡移民开始入迁山东。在20天内,将有735户3046名三峡移民正式迁徙到我省。2000年,作为试点,我省的广饶县接收了首批来自三峡库区重庆忠县的611位移民。2002年,我省的济南、青岛、烟台、潍坊、威海、济宁、淄博、泰安等市共接收安置了7049名三峡移民
2023-12-04 阅读 (80) -

三峡移民成功了吗(摄影师记录三峡移民27年)
2019年冬天,一张一个男人背着一树桃花的照片,忽然出现在互联网上,击中了许多中国人的心。照片的主人公,是来自湖北秭归县郭家坝镇的山民,刘敏华。十年前的春天,作为三峡库区移民的刘敏华,「在与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永别时,小心翼翼地带上了家门口的一棵桃树」。 ①屋檐下静默的男人,和他狭长背篼里那株盛放的桃花,激起观看者胸中无限心事。
2023-09-26 阅读 (27) -

关于三峡移民的书籍有什么作用(共续三峡移民情)
为加深人民对“三峡移民精神”的了解,更好地宣传三峡移民精神,让三峡移民精神深入到群众中去,坚定文化自信,提升文化认同感,重庆人文科技学院“志愿青春行,共续万州情”三下乡社会实践团于2023年7月18日于万州三峡移民纪念馆进行社会实践。图为实践团观看三峡移民纪念馆相关书籍 王世馨 供图“志愿青春行,共续万州情”三下乡社会实践团进入三峡移民纪念馆后,通过相关书籍以及文献资料了解到了三峡移民全过程;从最初制定三峡计划、移民方针,到移民试点、依法移民,再到移民搬迁、安置规划,以及后续工作安排、库区产业发展……无不
2023-10-19 阅读 (29) -

三峡移民到什么地方(移民浪潮中,三峡人迁徙至何处)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在一代代人接续奋斗的征程上我们已走过千山万水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同步推出“历史上的今天”栏目钩沉那些已然过去的“今天”启迪新时代的奋斗者今天“仍需跋山涉水”在新征程上再创荣光2000年8月17日首批三峡移民抵崇明:到家了!2000年8月17日,由重庆市云阳县启程来沪的首批150户、639位三峡库区移民,乘坐长江“江渝9号”轮安抵上海崇明,并于中午全部到达新居安顿落户。
2023-09-17 阅读 (64) -

三峡移民到广东有多少人(广东接纳了多少三峡移民)
“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1993年,全世界最大的移民工程---三峡移民轰轰烈烈开始了。为了支援三峡建设,长江两岸共有20多个县、277个乡镇、1680个村、将近130万库区人民,挥泪作别故土,叩别祖先,像漫天的尘埃,从此落尽了全国各地。他叫刘敏华,湖北秭归县郭家坝镇人。身为三峡移民的他,正要将自己的家搬往另一处,不久后他的祖屋即将沉入水底。
2023-10-23 阅读 (88)
热门资讯
-
 2023-10-13 阅读 (156)
2023-10-13 阅读 (156) -
 2023-10-17 阅读 (147)
2023-10-17 阅读 (147) -
 2023-10-18 阅读 (90)
2023-10-18 阅读 (90) -
 2023-10-23 阅读 (88)
2023-10-23 阅读 (88) -
 2023-12-04 阅读 (80)
2023-12-04 阅读 (80)
随机推荐
最新资讯
-
 2023-12-27 阅读 (17)
2023-12-27 阅读 (17)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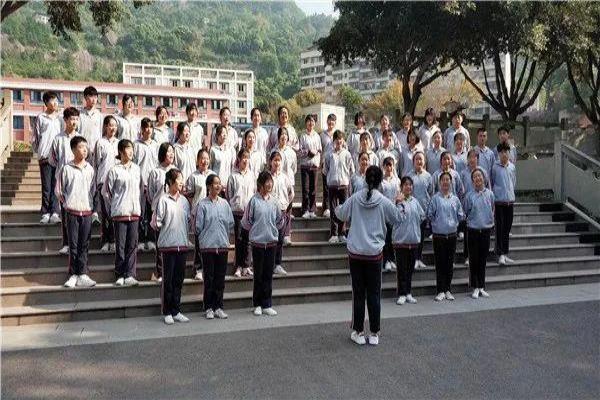 2023-12-26 阅读 (21)
2023-12-26 阅读 (21) -
 2023-12-22 阅读 (21)
2023-12-22 阅读 (21) -
 2023-12-21 阅读 (25)
2023-12-21 阅读 (25) -
 2023-12-21 阅读 (26)
2023-12-21 阅读 (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