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移民哪个省最多(哪个省份的三峡移民人数最多)
腊月,位于广东省肇庆四会市城中街道河西村委的西合村,沉浸在节前的喜庆节氛中。
村民刘廷雄已开始忙碌起来了,他采购了一批重庆特色年货,等着儿孙回来一起过在广东的第21个春节。
20年前,刘廷雄等703名来自重庆巫山县大昌镇的三峡移民离别故土,乘坐专列直抵肇庆四会大沙火车站,开始了新广东人的生活。20年来,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移民们用勤劳的双手、辛劳的付出,重建起新的美丽家园。

20年前三峡移民进入西合村场景 许接英翻拍
最好的回忆都在故土
腊肉、腊猪脚、红薯粉、干土豆……农历腊月二十二(1月24日),肇庆四会市西河村,刘廷雄赶在“小年”前到集市上的重庆特产店采购了一批年货。中午时分,在家门口和儿子贴着新对联的刘廷雄闻到了厨房里飘出的熟悉香味,那是妻子在为过年准备炸酥肉、腊肠、抄手等家乡传统小吃。
移民广东二十载,刘廷雄一家依旧保留着巴山乡民传统的过年习俗。
从2001年8月开始,来自重庆市巫山县的683户、共2400多位三峡移民,分三批先后落户肇庆市大旺、高要、四会三地的移民新村。其中四会市接收的703名移民,一批次集中迁入了东城街道、城中街道、贞山街道、大沙镇等四个镇(街道)六个安置点。
40岁的刘廷雄连同整个家族共10口人迁徙到西合村,从此在岭南水乡扎根。

刘廷雄夫妇 许接英/摄
20年过去了,无论对于60后刘廷雄,还是对于80后何勇来说,最好的回忆都在故土。
在当年肇庆四会市接纳的三峡移民中,中小学生有111名。为了让他们尽快适应新的学习环境,当地政府采取了“到就近学校插班”的方法,并指定素质较高的老师和优秀学生对移民学生进行帮助。时年14岁的何勇就是其中之一。移民到四会时,他刚读初一。
因家庭困难,何勇读完初中后曾想过出来打工,没想到政府得知情况后,资助他就读肇庆技校学习计算机。中专毕业后,他又自学成人大专、参加技能培训,先后考取国家理财规划师、安全主任等证书。
当年懵懂的孩子,如今已经是广东宝冠板材科技有限公司总助。四会给了何勇成长的平台,但浓浓的乡情始终牵绊着他。
由于亲人都在重庆,老家有红白事何勇都会驾车回去;老乡来广东打工,也会先来何勇这里走亲戚。“这是一种说不说道不明的感觉,年纪越大对家乡越怀念”。
新生活远比想象中顺利
移民前,刘廷雄有过多番顾虑,也做好了放下村支书的“身段”去工厂看大门的准备。但来到四会后,他发现新生活开展得比想象中顺利。
落户西合村不久,刘廷雄被介绍到城中街道水管站工作,这一干就是20年。他的妻子也没闲着,看准周边工厂林立、务工人员多的好商机,在家门口开起了麻将馆、士多店。一家人有了不错的收入,小日子越过越红火。
移民前,许志栖曾在惠州闯荡多年,拖家带口搬迁到四会和兴村后,有了地利之便,他挣钱养家的劲头更足了。
这些年,他做过厨师、卖过废品、搞过运输,碰过不少壁吃了不少苦,也在一次次创业中积累下不少经验,最终他组建起一个装修施工队,还在这边买房置业。回忆这20年打拼经历,已到知命之年的许志栖用一句话概括,“都是为了生活。”

许志栖采购粮油准备过年 受访者供图
20年来,为了保证三峡移民“搬得出,稳得住,逐步能致富”,四会市政府专门制定了一系列经济帮扶措施和优惠政策。如今他们已渐渐融入当地生活,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家住新昌村的王后艳和李忠春和大多数移民一样,在政府的就业帮扶下进厂打工。
“找工作更容易了,上班也方便很多。”移民前,王后艳曾在深圳观澜打过工,只有逢年过节才回重庆老家与亲人团聚,从没想过能在打工地安家落户。移民后,王后艳打工攒了钱,将政府提供的一层平房加盖至两层,多余的房间用来出租,实现了从打工妹到房东的角色转换。
同样衣食无忧的李忠春,在家门口的皮具厂工作。对于现在的生活,她感到很满足,在当地出生的小女儿不用做留守儿童更是让她倍感欣慰,“女儿从小就带在身边,很懂事,和我的感情很好。”

李忠春(右)在离家不远的工厂上班 许接英/摄
四会市水利局副局长杜智刚介绍,四会各移民村已经实现了进村道路、村中巷道硬底化,道路旁绿化,村村通自来水,有线电视数字化,通讯线路、供电线路到村到户。人均宅基地面积、房屋面积、土地资源均与当地居民生活水平基本持平。目前当地正在有序开展原三峡移民房屋重建工程,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标准,为移民打造新家园,预计2023年可建成入住。
融入,是在不知不觉中不分彼此
20年光阴转瞬即逝,对于老家的印象,刘廷雄已逐渐模糊。他喜欢称自己为半个“老广”——辣椒吃得越来越少,“老豆”二字脱口而出,小儿子娶的也是四会本地姑娘。“孩子现在在肇庆一家企业做技术员,入职没几个月就当了班长,基本工资有8000元。”说起儿子,他一脸笑容。
移民后,刘廷雄只在2008年回过一趟老家,那是为了给去世多年的父亲立碑。大儿子结婚时,他也曾摆下80桌酒席,宴请四会、高要、江门等周边的三峡老乡一起热闹热闹。如今,刘廷雄计划退休后回老家仔细走走,看看三峡大坝。
随父母迁徙到昌辉村时,李俊杰只有六岁,那时他听不懂广东话。后来,学校发书让大家学习,不到三个月,他就说出了一口流利的广东话。
每年清明节,李俊杰一家会和当地人一样祭拜祖先;春节时,李俊杰也会和本地好友组团“逗”利是……如今已26岁的他视自己为新四会人,他的父母也和当地村民融成一片,有空一起去跳广场舞。

李俊杰大学毕业后回到四会当老师 受访者供图
大学毕业后,心存感恩的李俊杰回到四会成为一名人民教师,这是他从小就立下的志愿,“我爱这座城,政府对我们这么关照,我们也要为这座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回报自己的力量。”
相关文章
-

三峡移民是哪些地方迁移出去的(三峡工程的移民都去了哪里)
【关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使,及时获取国际教育,科技,文化,经济及世界语(esperanto)最新资讯】三峡工程是世界上最大的水电工程,其建设时间之长、建设难度之大、涉及难题之多,是全世界范围内都不曾遇到过的。这其中,最大的困境,恐怕还在于水库修建区域的大量居民应该如何疏散。上百万人,背井离乡,如果得不到很好的安置会成为巨大的不稳定因素,而如果妥善安置则不仅能完成项目,还能作为中国管理水平的样本以鉴后世。
2023-10-03 阅读 (31) -

三峡移民上海多少人(百万三峡移民)
重庆日报全媒体龙丹梅110多万移民告别故土,2座城市、7座县城、94座集镇迁建,1400家工矿企业搬迁……这不是一组简单枯燥的数字,这是重庆为三峡工程按期蓄水、通航、发电作出的巨大牺牲和贡献!三峡工程成败的关键在移民,而移民的重点在重庆,重庆承担着85%以上的三峡移民任务。自三峡工程移民搬迁安置工作启动到全面完成移民搬迁安置任务,重庆累计搬迁安置移民110万余人。
2023-11-08 阅读 (20) -

三峡移民后来怎么样了(摄影师记录三峡移民27年)
2019年冬天,一张一个男人背着一树桃花的照片,忽然出现在互联网上,击中了许多中国人的心。照片的主人公,是来自湖北秭归县郭家坝镇的山民,刘敏华。十年前的春天,作为三峡库区移民的刘敏华,「在与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永别时,小心翼翼地带上了家门口的一棵桃树」。 ①屋檐下静默的男人,和他狭长背篼里那株盛放的桃花,激起观看者胸中无限心事。
2023-10-30 阅读 (26) -

三峡移民多少人移到上海(现状让人疑惑)
67岁移民夫妻在上海浦东新区住450平洋房,千万补偿不愿意拆迁?如今为何一天要打三份工?22年与千里之外的80岁老母亲一面都不见,是什么缘故?最近在上海浦东新区惠南镇某村游玩,听说附近有移民村,就是从三峡那边搬迁过来的移民,想去采访一下他们,看看他们如今过的怎么样。在一位热心大姐指引下,我找到了这户移民家的房子,第一眼看到房子的时候,我就很惊讶,三层的洋房上上下下透露着富贵和大气,我迫不及待想要采访一下这户人家。
2023-11-23 阅读 (48) -

三峡移民纪录片有哪些
五月初的涪陵,时阴时雨时艳阳,天气就象一个正值青春期的少年,时不时的要耍耍小性子。凌晨4点多,睦和村还在大江的臂弯中沉睡,我和导演一行人等便匆匆告别周公,披着满天星斗上路了。睦和村的日出是导演张道伟想要捕捉的镜头。伟哥是个有思想有情怀的导演,一米八三的身材高魁伟岸,我曾戏言他的体积有175的库容,这也是三峡大坝蓄水时的最高水位线。
2023-12-03 阅读 (19) -

三峡移民移到哪了(他们移向了哪里,如何重新扎根)
【关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使,及时获取国际教育,科技,文化,经济及世界语(esperanto)最新资讯】三峡工程是世界上最大的水电工程,其建设时间之长、建设难度之大、涉及难题之多,是全世界范围内都不曾遇到过的。这其中,最大的困境,恐怕还在于水库修建区域的大量居民应该如何疏散。上百万人,背井离乡,如果得不到很好的安置会成为巨大的不稳定因素,而如果妥善安置则不仅能完成项目,还能作为中国管理水平的样本以鉴后世。
2023-10-11 阅读 (61) -

关于三峡移民的书籍有什么作用(共续三峡移民情)
为加深人民对“三峡移民精神”的了解,更好地宣传三峡移民精神,让三峡移民精神深入到群众中去,坚定文化自信,提升文化认同感,重庆人文科技学院“志愿青春行,共续万州情”三下乡社会实践团于2023年7月18日于万州三峡移民纪念馆进行社会实践。图为实践团观看三峡移民纪念馆相关书籍 王世馨 供图“志愿青春行,共续万州情”三下乡社会实践团进入三峡移民纪念馆后,通过相关书籍以及文献资料了解到了三峡移民全过程;从最初制定三峡计划、移民方针,到移民试点、依法移民,再到移民搬迁、安置规划,以及后续工作安排、库区产业发展……无不
2023-10-19 阅读 (29) -

三峡移民安徽哪个村最好找工作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融媒体系列报道《我和我的党支部》 今天,为您带来由湖南电台携手重庆市万州区广播电视台等全国100家电台采制的《五溪村党支部:带领三峡移民“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人间最美四月天。在重庆市万州区新田镇五溪村,满目果树繁茂,阵阵花果飘香,一江碧水,两岸青山,一副生机盎然的山水画卷展现在前来采摘的游客面前。
2023-09-28 阅读 (42) -

三峡移民到山东哪个市(铭记百万移民的故事)
重庆三峡移民纪念馆外观 本文图片均由重庆三峡移民纪念馆提供东汉灰陶庖厨俑“三峡外迁移民第一人”徐继波捐赠的外迁船票以身殉职的巫山移民干部冯春阳生前用品以身殉职的巫山移民干部冯春阳生前用品正是三峡库区最美的时节,高峡出平湖,碧绿长江滚滚而来。江水之畔,矗立着一座巨石般的建筑,这就是重庆三峡移民纪念馆(重庆市万州区博物馆)。
2023-12-15 阅读 (21) -

三峡移民到广东有多少人(广东接纳了多少三峡移民)
“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1993年,全世界最大的移民工程---三峡移民轰轰烈烈开始了。为了支援三峡建设,长江两岸共有20多个县、277个乡镇、1680个村、将近130万库区人民,挥泪作别故土,叩别祖先,像漫天的尘埃,从此落尽了全国各地。他叫刘敏华,湖北秭归县郭家坝镇人。身为三峡移民的他,正要将自己的家搬往另一处,不久后他的祖屋即将沉入水底。
2023-10-23 阅读 (88)
热门资讯
-
 2023-10-13 阅读 (155)
2023-10-13 阅读 (155) -
 2023-10-17 阅读 (147)
2023-10-17 阅读 (147) -
 2023-10-18 阅读 (90)
2023-10-18 阅读 (90) -
 2023-10-23 阅读 (88)
2023-10-23 阅读 (88) -
 2023-12-04 阅读 (80)
2023-12-04 阅读 (80)
随机推荐
最新资讯
-
 2023-12-27 阅读 (15)
2023-12-27 阅读 (15)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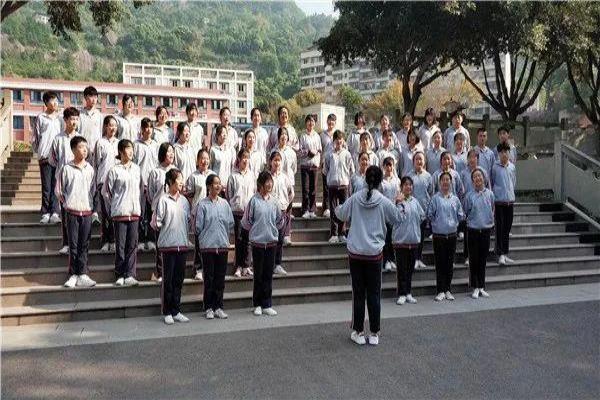 2023-12-26 阅读 (21)
2023-12-26 阅读 (21) -
 2023-12-22 阅读 (21)
2023-12-22 阅读 (21) -
 2023-12-21 阅读 (25)
2023-12-21 阅读 (25) -
 2023-12-21 阅读 (26)
2023-12-21 阅读 (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