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三峡移民到外地(库区外迁移民)
三峡库区农村外迁移民车队
2000年8月13日,是个令人难忘的日子。
这一天,重庆三峡库区首批7000多外迁移民,在各级政府精心组织下告别祖祖辈辈休养生息的故土,走向新生活。
这一天,重庆三峡库区数县的农村兄弟,扶老携幼,在送别的亲友簇拥下,一步三回头,乘上汽车,坐着轮船,奔赴陌生的天地……

别了,我的乡亲
哦,移民,这是政府决策啊!举世瞩目的三峡工程竣工之时,将有百万居民撤离世代定居地,在人均仅有0. 8亩土地的穷山恶水寻觅新的生存环境和生活空间。“就地后靠”曾经是“故土难离”的一种正面诠释。但坡耕地上的劳作效益较之于环境植被的破坏,“得不偿失”这四个字将演绎成水土流失加剧后长江中下游频率更高的“严防死守”。更为严竣的现实是,30多年的“不上不下”,国家在三峡库区的重点项目投资几乎为零;而“不三不四”的现状又使库区各县市宛若后娘养的“孩子”,当地政府无钱投资,工矿企业发展严重“贫血”,库区老百姓在贫困里挣扎,是不争的事实。

忠县:移民外迁船队
与其守穷,莫如外迁。国务院适时对三库移民的安置政策作出重大调整:2003年6月前,将库区农村移民近1/3外迁至上海、广东、江苏、浙江、福建、山东等11个省市安家落户,前提是:接收地土地资源丰富,经济较发达。
政策如阳光雨露,播洒在三峡库区,滋润着12万农村移民兄弟的心田。难舍故土的离愁在胸间弥漫,对新生活的希冀亦在心中发芽……
哦,明天,明天将是启程的日子啊!
祖先的墓地前,匍匐着虔诚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点点白幡摇晃着无尽的哀思,滴滴乡愁燃点着恩怨炸响在峡江两岸的山坡,我的移民兄弟啊,你们在诉说什么?

移民船队

没看见已收割的自留地里,主人仍在凝望、仍在来回走动的身影么?
没看见已搬空的残墙内,主人仍在熟悉的方寸之间徜徉,用粗糙的双手抚摸着、侍弄着什么吗?
哦,8月13日的阳光,终于在难捱的等待里普照峡江两岸。
送别的码头上、汽车旁、相拥痛哭的母女话语哽咽……他们将故乡情、同志爱凝成泪珠,洒在送别的仪式里,溶入外迁的移民睡梦中,化作无声的牵挂和真诚的祝福。

移民船队过葛洲坝船闸
哦,一撮泥土,被主人包裹着上船,从此,一缕缕乡思在船仓弥漫;
哦,一株小树,被主人怀抱着上车,从此,故乡的树荫在车内伞状扩散……
带上一包种子吧,带上一罐故乡的水吧,我们的移民兄弟!有了种子有了水,还愁故乡的作物不能在异地生长么?要知道,故乡的种子里,蕴含着故乡人民的关爱啊!
送别不是永别,流泪不全是悲伤。我的移民兄弟啊,你们是12万同胞兄弟的先行者,在你们的目的地,同样有无数双期盼的目光,正在向你们聚焦。

外迁老姐妹
放心地走吧,我的移民兄弟!你们以“舍小家,为大家”的情怀外迁他乡,三峡工程不会忘记,我们的人民共和国不会忘记!
相关文章
-

三峡移民概况(三峡移民走过26年)
如果说,三峡工程是一座历史丰碑,三峡移民就是托起这座丰碑的基石;如果说,三峡工程是世界水利史上的奇观,三峡移民就是创造这一奇观的民族工匠。从1992年到2018年,秭归移民搬迁建设长达26年。今天,站在世纪工程的肩膀上,眺望雄伟的三峡大坝和高峡平湖胜景,回首三峡移民26年沧桑岁月,一幕幕三峡移民告别故土、抛家舍园的动人情景,一幅幅屈乡儿女艰苦奋斗、重建家园的恢弘画面,象奔腾不息的长江水在我们心中涌动。
2023-10-20 阅读 (26) -

三峡移民纪录片有哪些
五月初的涪陵,时阴时雨时艳阳,天气就象一个正值青春期的少年,时不时的要耍耍小性子。凌晨4点多,睦和村还在大江的臂弯中沉睡,我和导演一行人等便匆匆告别周公,披着满天星斗上路了。睦和村的日出是导演张道伟想要捕捉的镜头。伟哥是个有思想有情怀的导演,一米八三的身材高魁伟岸,我曾戏言他的体积有175的库容,这也是三峡大坝蓄水时的最高水位线。
2023-12-03 阅读 (20) -

三峡移民移到哪了(他们移向了哪里,如何重新扎根)
【关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使,及时获取国际教育,科技,文化,经济及世界语(esperanto)最新资讯】三峡工程是世界上最大的水电工程,其建设时间之长、建设难度之大、涉及难题之多,是全世界范围内都不曾遇到过的。这其中,最大的困境,恐怕还在于水库修建区域的大量居民应该如何疏散。上百万人,背井离乡,如果得不到很好的安置会成为巨大的不稳定因素,而如果妥善安置则不仅能完成项目,还能作为中国管理水平的样本以鉴后世。
2023-10-11 阅读 (64) -

三峡移民是政策移民吗(移民补助咋发放)
人民网武汉2月26日电 (王郭骥)近日,有网友通过人民网“领导留言板”向湖北省枣阳市委书记留言,反映父亲的移民补助发放问题。2月22日,枣阳市刘升镇人民政府回复,600元移民款已经于2022年1月25日足额到账。据了解,摆某智系枣阳市刘升镇刘升村三组居民、水库移民,按照大中型水库、三峡库区的农村移民每人每年600元的标准进行补助。
2023-12-21 阅读 (26) -

三峡移民安徽哪个村最好找工作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融媒体系列报道《我和我的党支部》 今天,为您带来由湖南电台携手重庆市万州区广播电视台等全国100家电台采制的《五溪村党支部:带领三峡移民“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人间最美四月天。在重庆市万州区新田镇五溪村,满目果树繁茂,阵阵花果飘香,一江碧水,两岸青山,一副生机盎然的山水画卷展现在前来采摘的游客面前。
2023-09-28 阅读 (43) -

三峡移民搬到上海什么地方(20年前三峡移民到上海)
引言采访三峡外迁上海的移民中,刘叔是我遇到的一位态度非常“强硬”的人,采访过程中,刘叔甚至直接喊出,我就是上海人,我死都要死在上海。而关于他的故事,也让我非常感动,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他的故事吧。今天我来到上海嘉定区的娄塘镇,据说这里在2004年的时候,接收了很多来自三峡库区的移民。2004年 9月1日,重庆云阳县的刘建军(故事里我们称刘叔)背着龙凤胎儿女抵达上海。
2023-11-08 阅读 (31) -

外地的户口可以迁到洛阳吗(河南洛阳西工分局)
“您好,现在是暑期办证高峰期,办理人员较多,请您稍作休息,我们会为您尽快办理”。进入6月,随着高考结束,端午节、暑假临近,河南省洛阳市公安局西工分局政务服务大厅迎来市民申办出国(境)证件的高峰。6月12日8时40分,西工分局政务服务大厅外已经排起了长队。“请问驾照体检业务是在这里办理吗?”“护照到期了怎么换?
2023-09-23 阅读 (43) -

三峡移民户口可以迁到其他城市吗?(20多年前的三峡外迁移民)
前言三峡移民外迁是中国历史上的一项重大工程,为了解决三峡库区的贫困问题,数以万计的人们选择离开家园,迁往全国各地。20多年过去了,如今我们来看,当时的选择是否明智?在重庆的人们是否比外迁的人们更幸福?本文将从不同角度来探讨这一问题。外迁的库区人们一、当时的选择三峡库区在工程建设之前一直是一个相对贫困的地区,受淹影响,人们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
2023-10-25 阅读 (24) -

三峡移民四川多少人(8000多万的四川人都来自哪里)
孙大侃 丨作者导读:为什么说四川人是独一无二的?即便上网搜索“四川人”,也没有多少人能说明白。一些学者将四川人与北方人和南方人作了一番比较后,干脆下了一个定义:不南不北四川人。还有说四川人是亦正亦邪构成的特殊材料,四川人的“邪”,可能是只有四川人才能领会的词,中性偏褒,并不是“邪恶”,而是含有不按常规出牌等含义。
2023-12-10 阅读 (51) -

三峡移民真实惨状(三峡移民,揭开背后的辛酸真相)
故乡是一座孤岛,成年后只能在他乡遥遥凝望。想念故乡的桃花树、想念村边潺潺的流水,可惜这些只能存在于回忆中。1992年,随着一纸文书的下发,100多万人的命运就此改变。在这100多万人眼中,故乡就是那长江三峡蜿蜒碧绿的江水。生产发展日趋完善,经济上升让人喜上眉梢的同时,环境保护也迫在眉睫。在国际发展大会中,联合国向各国提出建议,要保护自然环境,退耕还林,这样才能充分利用自然潜力,造福子孙后代。
2023-10-12 阅读 (34)
热门资讯
-
 2023-10-13 阅读 (156)
2023-10-13 阅读 (156) -
 2023-10-17 阅读 (148)
2023-10-17 阅读 (148) -
 2023-10-18 阅读 (91)
2023-10-18 阅读 (91) -
 2023-10-23 阅读 (89)
2023-10-23 阅读 (89) -
 2023-12-04 阅读 (81)
2023-12-04 阅读 (81)
随机推荐
最新资讯
-
 2023-12-27 阅读 (17)
2023-12-27 阅读 (17)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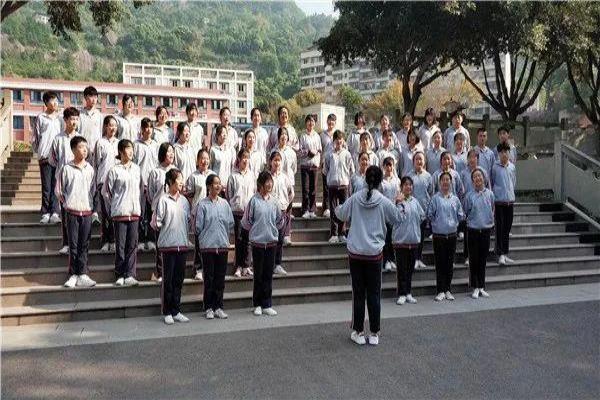 2023-12-26 阅读 (22)
2023-12-26 阅读 (22) -
 2023-12-22 阅读 (21)
2023-12-22 阅读 (21) -
 2023-12-21 阅读 (26)
2023-12-21 阅读 (26) -
 2023-12-21 阅读 (26)
2023-12-21 阅读 (26)